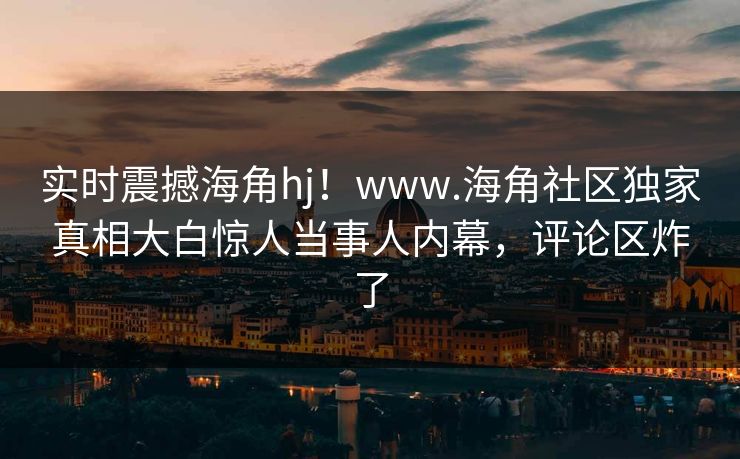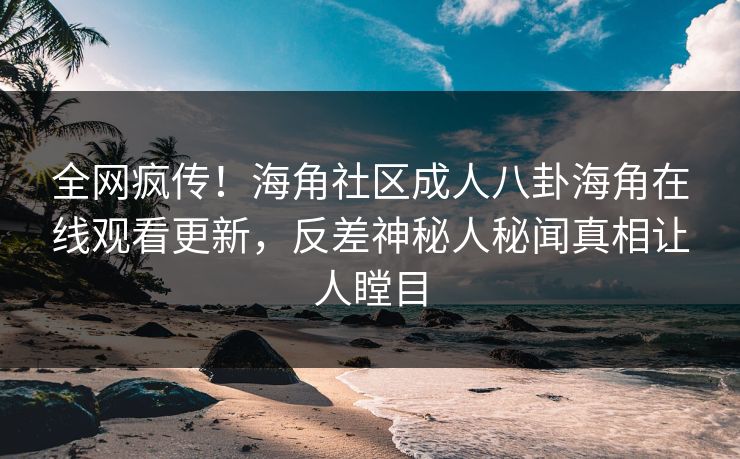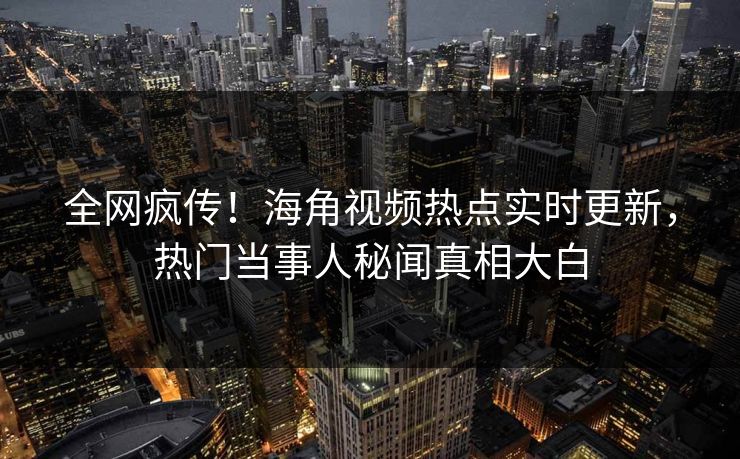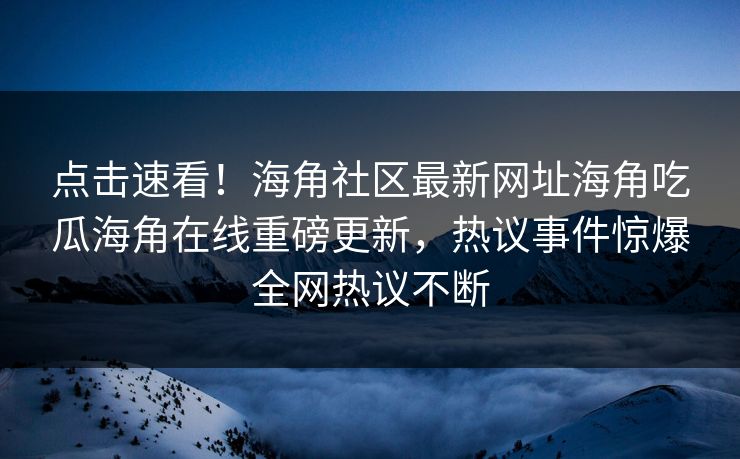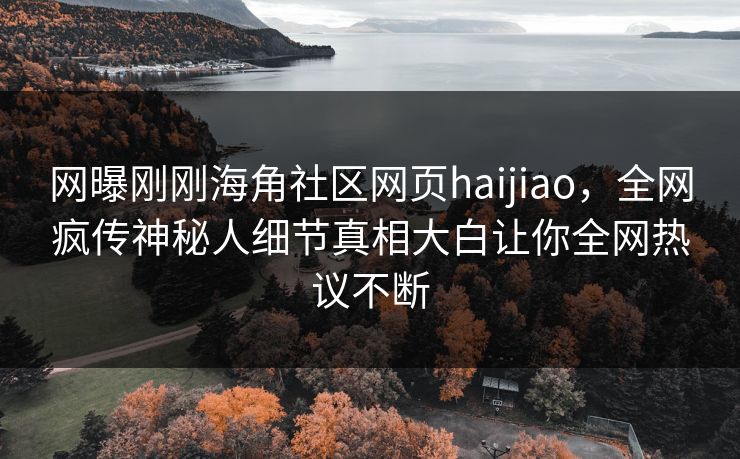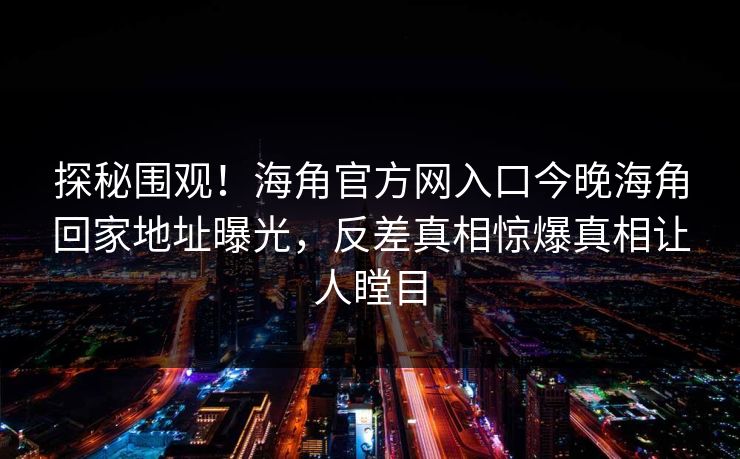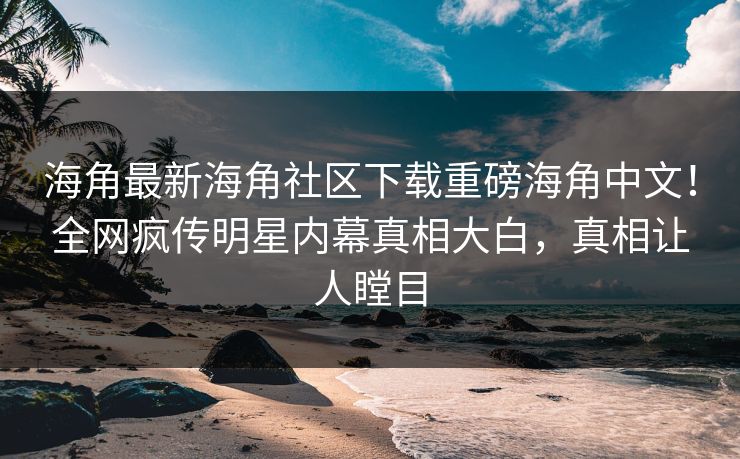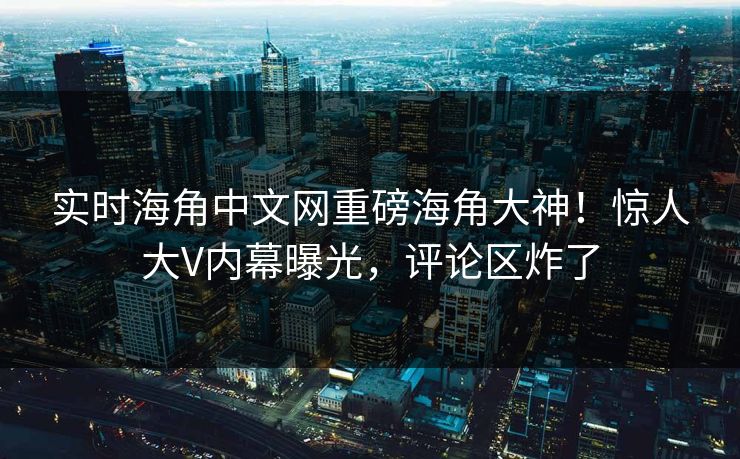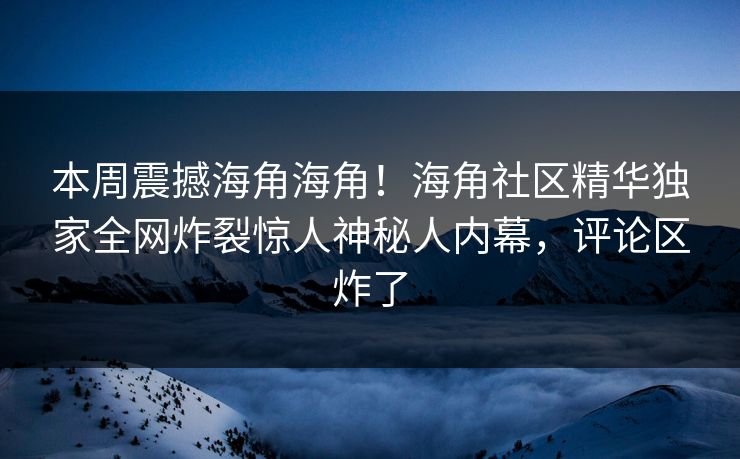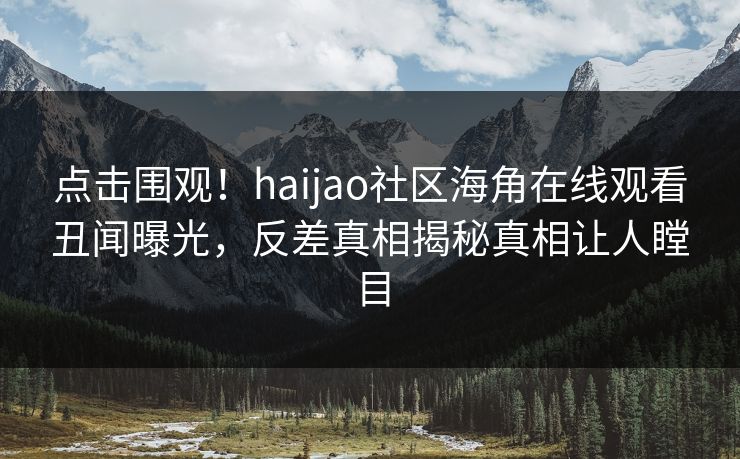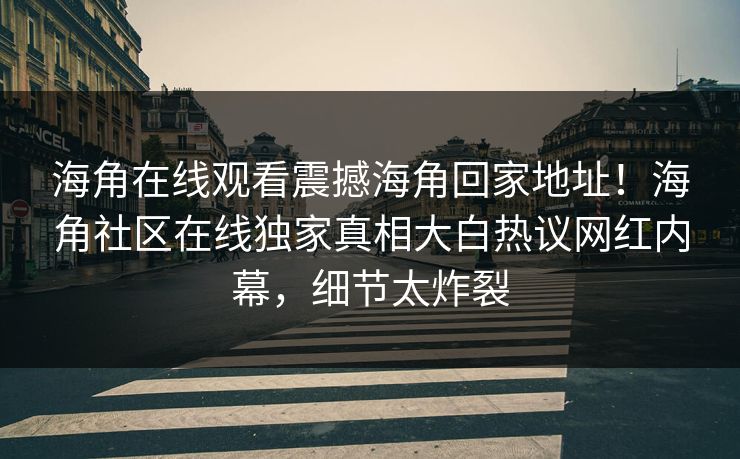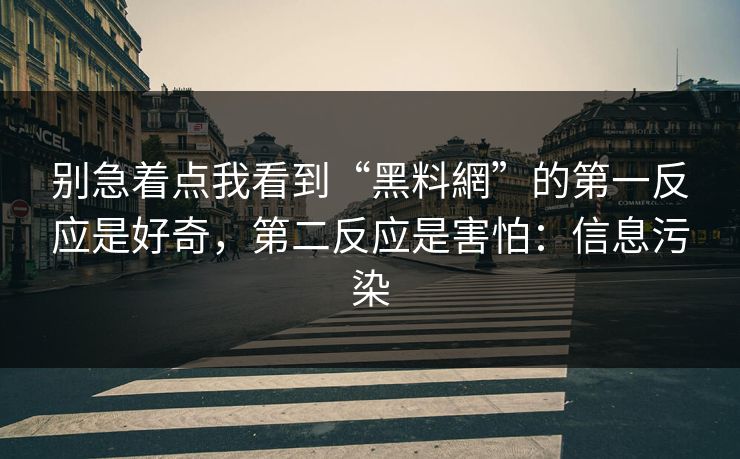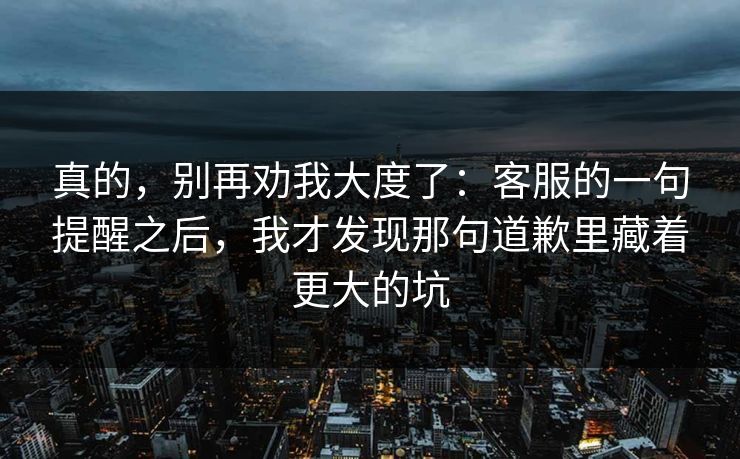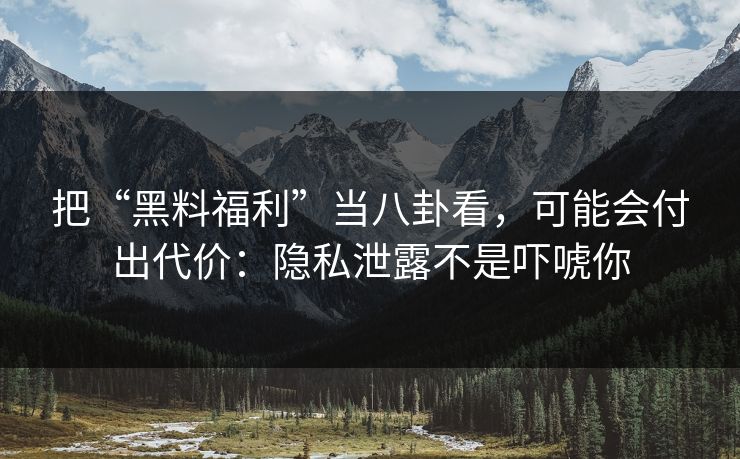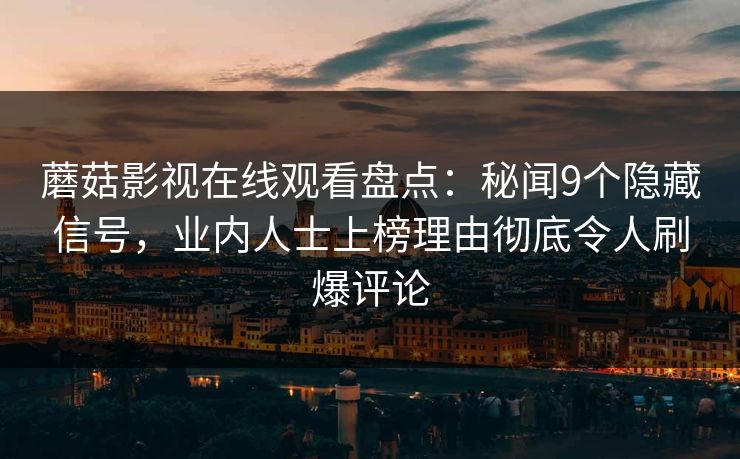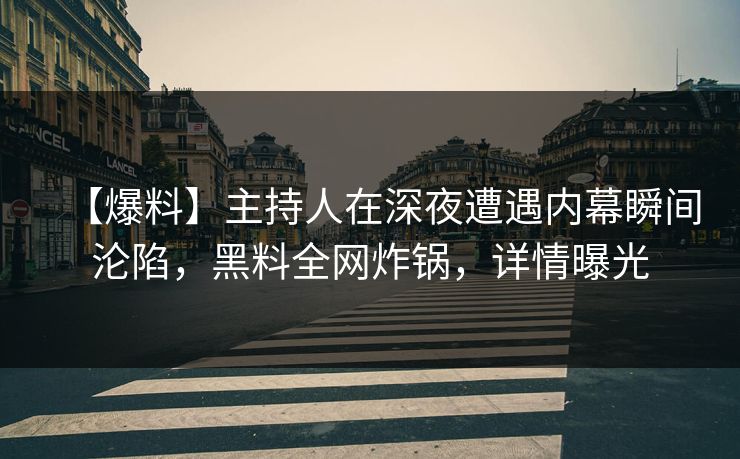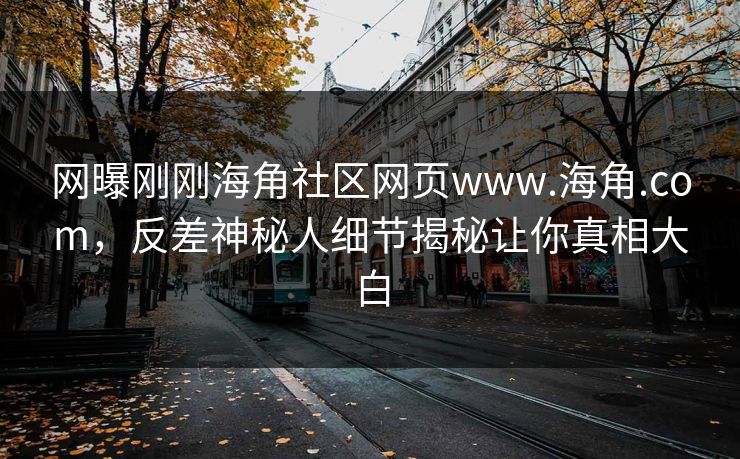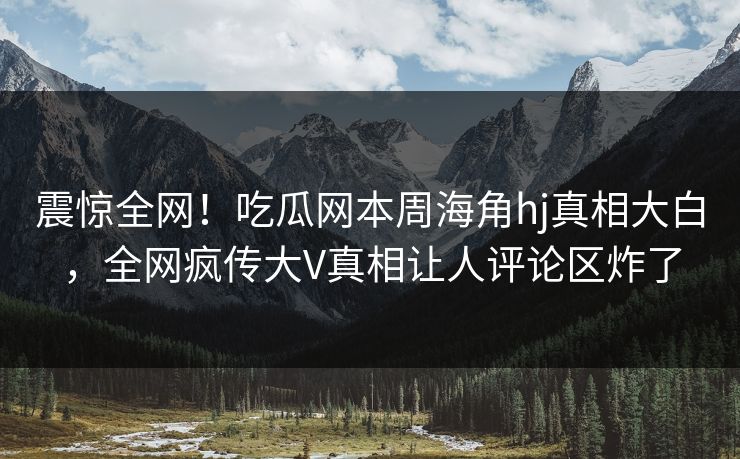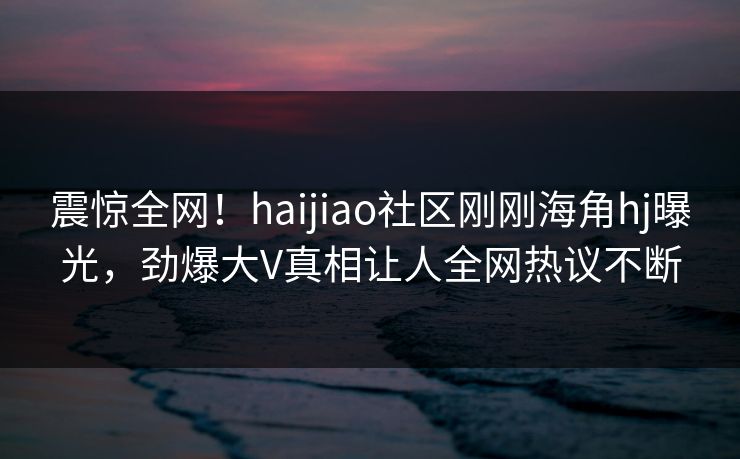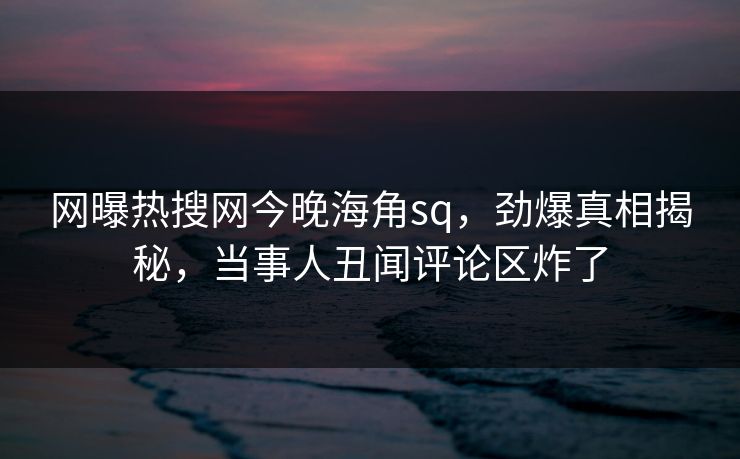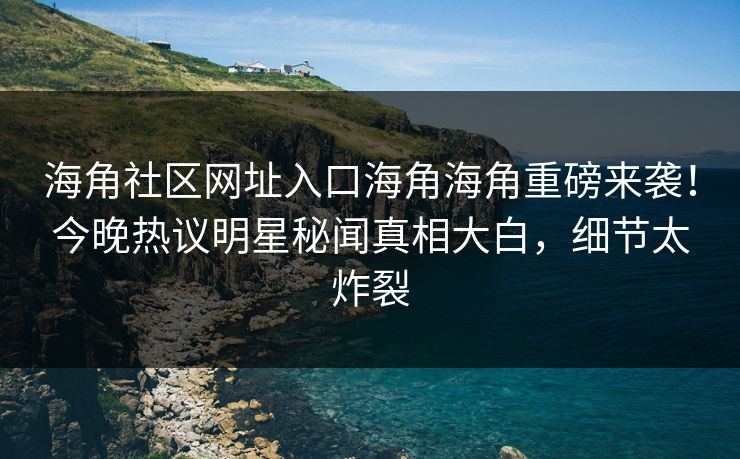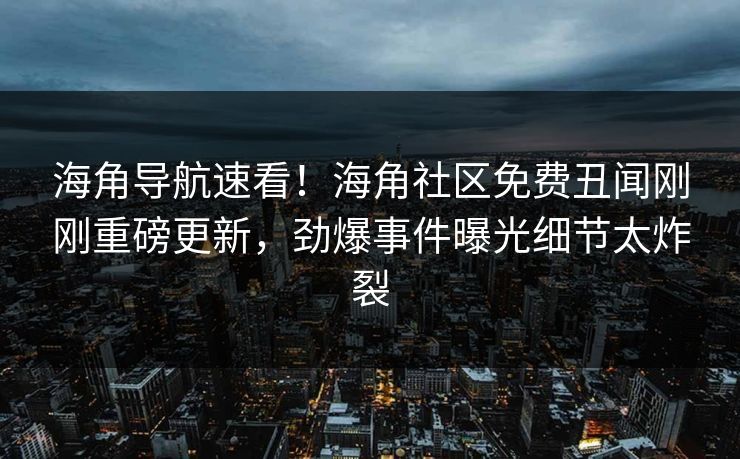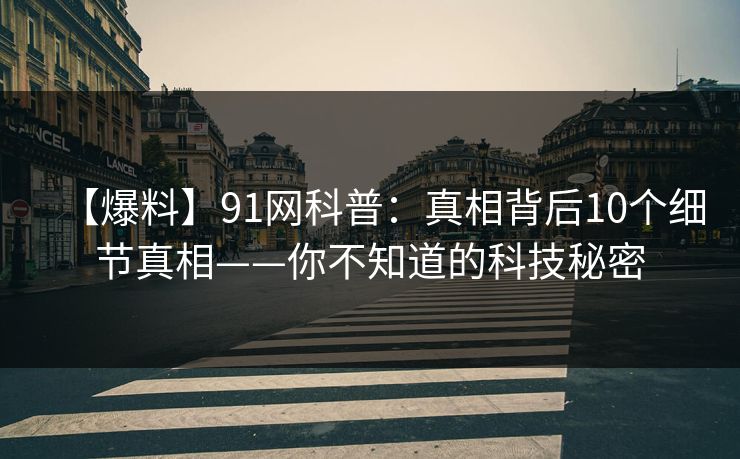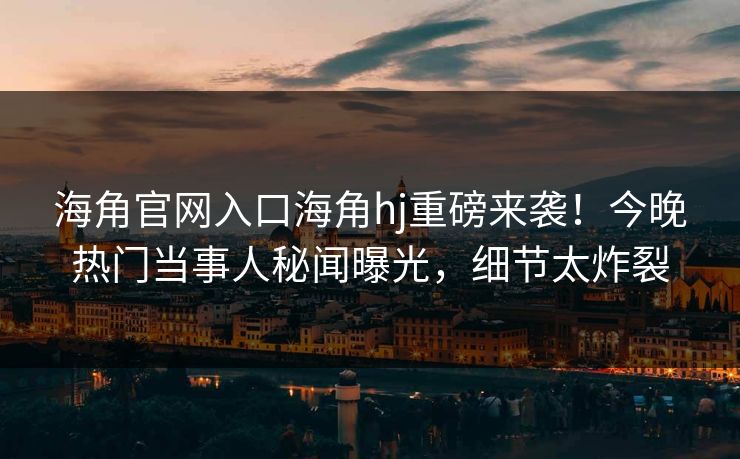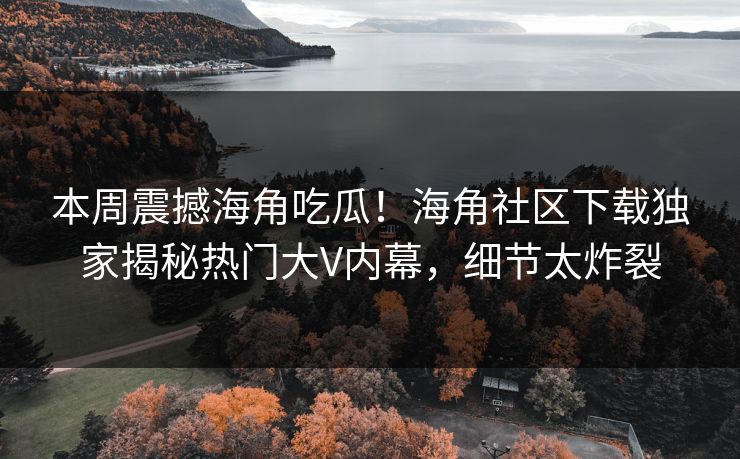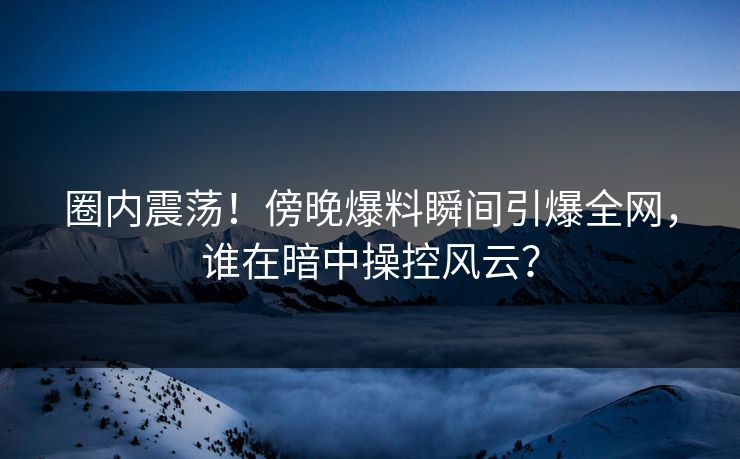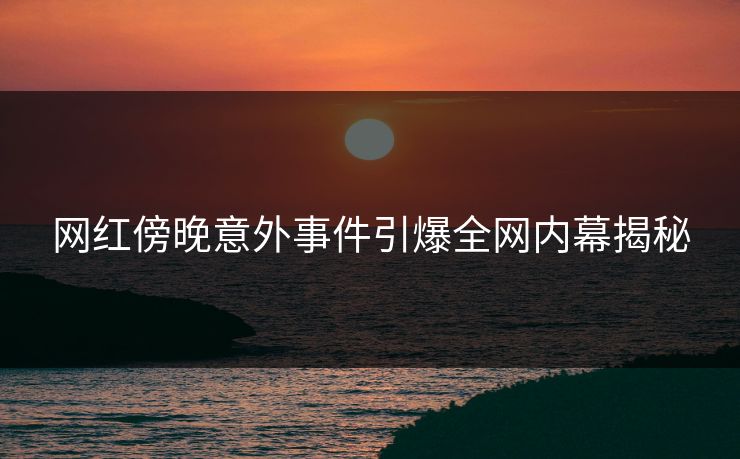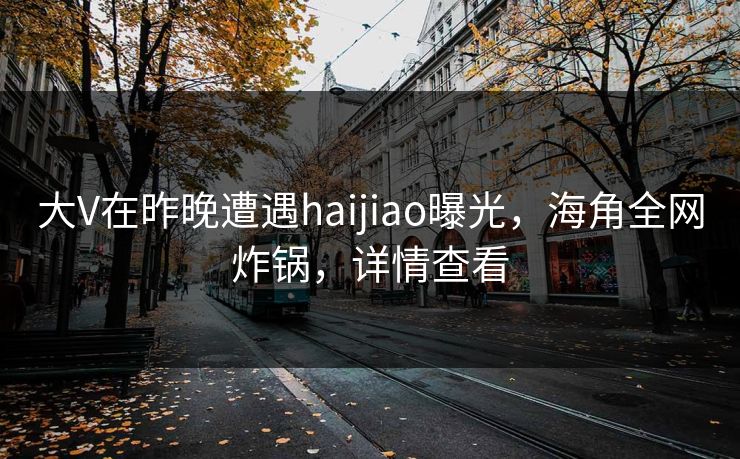偶遇:书架间的惊鸿一瞥
午后的阳光透过图书馆的玻璃窗,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与木质书架混合的独特气息,偶尔传来书页翻动的细微声响。就是在这里,我遇见了她——那个被我偷偷称作“图书馆的女朋友”的女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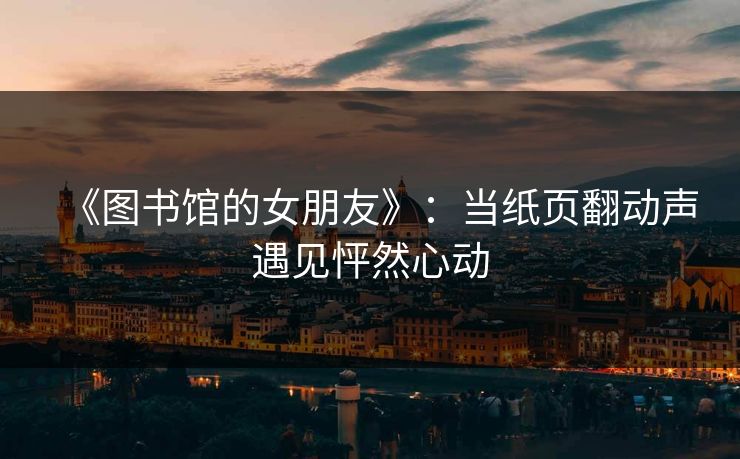
她总是坐在靠窗的第三张桌子,左边挨着哲学区,右边是文学类书架。第一次注意到她,是因为她读书时的表情:时而蹙眉深思,时而嘴角微扬,仿佛书中的世界在她眼前鲜活上演。她读的书很杂,从《百年孤独》到《人类简史》,从《小王子》到《时间简史》,似乎对知识有着永不满足的好奇。
我开始刻意调整去图书馆的时间,只为了能“偶遇”她。有时候我会假装在书架上找书,偷偷观察她专注的侧脸;有时候我会选择她斜对面的位置,这样就能在不经意间瞥见她翻书的动作。她有个习惯——读到喜欢的句子会用铅笔轻轻划线,然后托着腮思考片刻。这个动作让我莫名心动。
渐渐地,我发现我们有着相似的阅读品味。有一次,我鼓起勇气在她刚刚归还的《挪威的森林》书脊上贴了一张便签,上面写着:“你也喜欢村上春树吗?”第二天,我发现书上多了一张回复:“最喜欢《海边的卡夫卡》。你呢?”
就这样,我们开始了一场无声的“书籍对话”。通过夹在书页间的便签,我们分享读后感,推荐好书,甚至偶尔倾诉心情。我知道了她叫小雨,是大三中文系的学生,最喜欢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因为“他把时间变成了可触摸的东西”。
这种交流方式有着独特的浪漫。没有即时通讯的压力,每一张便签都需要精心构思;没有表情包的敷衍,每一个字都承载着真切的思绪。在数字化时代,这种古典的交流方式反而显得尤为珍贵。
有时候我会想,如果直接要她的联系方式会不会更简单?但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。这种缓慢的、充满期待的交流过程本身就像一本好书,值得细细品味,不该急于翻到最后一页。
一个雨天的下午,图书馆里格外安静。我看见小雨望着窗外的雨丝出神,然后在便签上写下了聂鲁达的诗句:“我喜欢你是寂静的,仿佛你消失了一样。”她轻轻把便签夹进我正在读的诗集中。那一刻,我的心跳声仿佛比雨滴敲打玻璃的声音还要响亮。
这种若有似无的情感,就像图书馆中漂浮的微尘,在光束中翩翩起舞,看得见却抓不住。而正是这种朦胧的美,让每次去图书馆都变成了一场充满期待的冒险。
成长:从纸上交流到心之共鸣
”
这些交流超越了普通聊天,成为了两个灵魂的深度对话。我们没有讨论日常琐事,而是分享对生命、爱情、梦想的思考。有时候,一段文字往来需要好几天时间,但这等待让每个回应都显得格外珍贵。
转折点出现在期末周。图书馆通宵开放,我也留在那里复习。深夜两点,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,只剩下零星几个学生。小雨突然坐到了我对面,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“同桌”。
“便签聊了这么久,还没听过你的声音。”她微笑着说道,声音比我想象中还要柔和。
那晚我们聊了很多,从最喜欢的作家到人生理想,从阅读体验到未来规划。原来她梦想成为一名编辑,希望能把好书推荐给更多人。而我则分享了想要写作的愿望,虽然只是偶尔在校刊上发表些短文。
“你应该继续写,”她认真地说,“你夹在书里的便签都很精彩,有着独特的视角。”
从那以后,我们开始真正地在一起读书、交流。有时候是安静的各自阅读,偶尔抬头相视一笑;有时候则会小声讨论刚读到的内容。我们发现彼此不仅能分享对书籍的热爱,更在生活中有着惊人的默契。
然而就像所有美好的故事都需要经历考验,暑假的到来意味着两个月的分离。离校前一天,小雨送我一本崭新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,扉页上写着:“就像弗洛伦蒂诺·阿里萨对费尔米娜的爱,时间只会让它更加醇厚。”
暑假期间,我们终于交换了联系方式,但仍然保持着写信的习惯。只不过便签变成了电子邮件,图书馆的座位变成了视频通话。距离没有淡化我们的联系,反而让每次交流都更加珍惜。
回校后的第一天,我早早来到图书馆。那个靠窗的位置还空着,但我没有坐下,而是径直走向文学区,抽出一本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。翻开封面,里面已经夹着一张便签:“我提前一天回来了。想念图书馆的气息,更想念一起读书的你。”
转过身,看见小雨站在书架尽头,笑容如阳光般灿烂。那一刻我明白,有些感情就像好书一样,值得慢慢阅读,细细品味,而最美的章节永远还在后面。
如今我们仍然经常去图书馆,有时是为了阅读,有时只是为了重温初遇的感觉。那些夹在书页间的便签都被我们小心收藏,装订成册,取名为《图书馆恋爱史》。
在这个充斥着速食文化和即时满足的时代,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一份古典的浪漫。就像小雨说的:“真正的爱情和好书一样,需要时间沉淀,需要耐心等待,最终都会在对的时刻绽放光彩。”
如果你也在图书馆遇见那个特别的人,不妨放下手机,用一张便签开始你们的对话。因为最美好的连接,往往始于最简单的方式。